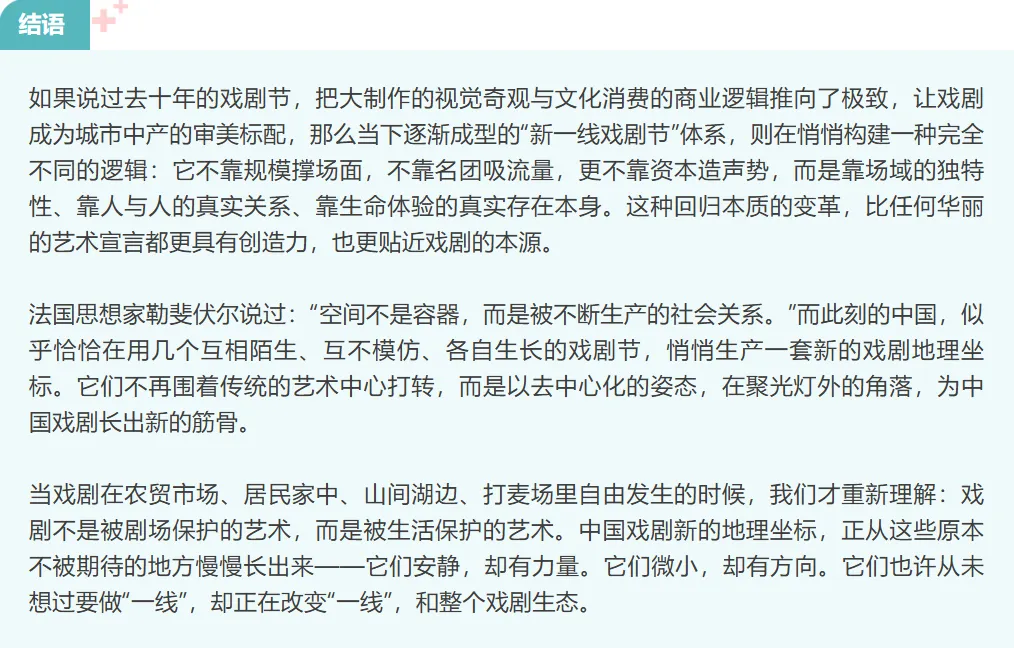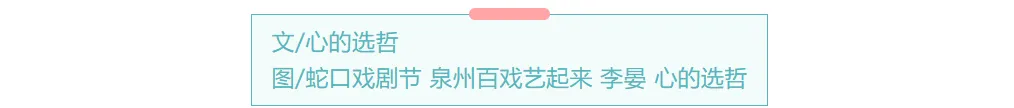- CN
- Login
2025年11月22日 媒体声音
从一线日常里长出来的“新一线”戏剧节
- 心的选哲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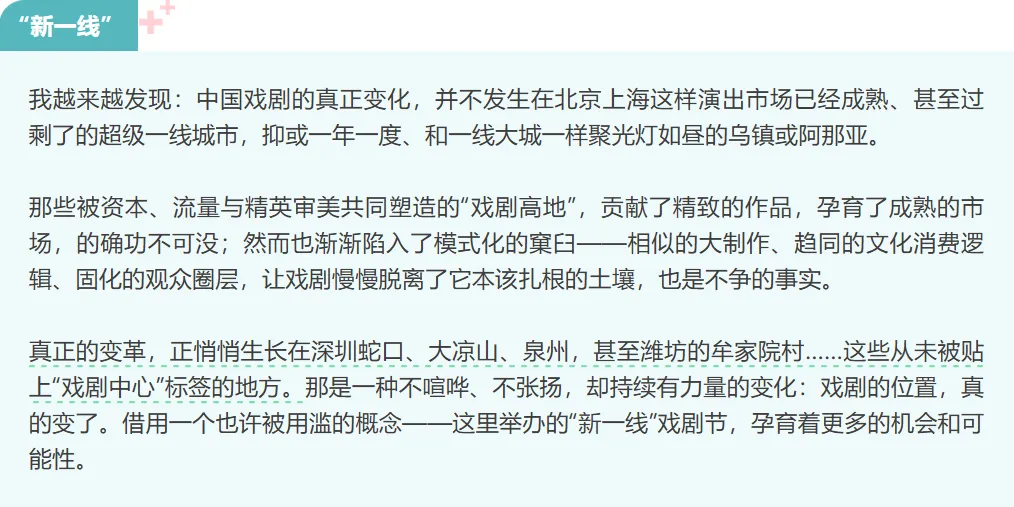

从蛇口戏剧节2022年呱呱坠地,我便一直追看它的“成长日记”。从最初觉得这里是“小众实验场”的好奇,到后来被作品打动的沉浸;再到今年,忽然生出一种清晰的认知:立足于“大湾区年轻戏剧孵化基地”的蛇口,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“实验场”,它不再满足于打破常规,而是沉淀出了一套可操作、可复制、有本土根基的戏剧方法论——一种关于“空间激活”的中国方案。
蛇口的特殊之处,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空间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“试管”,这里既有南海意库这样由旧厂房改造、有《外来妹》故事的文创园区,满是工业遗迹与商业活力的碰撞;也有热闹的农贸市场、密集的国内第一代商品房社区,保留着最鲜活的生活气息;还有地下车库、长廊、办公室这些被日常使用却从未被“观看”的公共空间。这些空间不是空白的画布,而是被历史、商业、生活填满的“饱和空间”,而蛇口的戏剧,就是在这些饱和的缝隙里,完成对空间的重新解读。

在今年的《继续航行 Yet so far》中,海上世界艺术中心的扶梯、橱窗、楼梯、长廊、露台、室外花园、地下车库……都被彻底重新分配了意义。身着白蓝色系衣/裙的演员,接力组成引导线如海浪一般,蜿蜒穿过原本用作演出之外、消费等各种功能的动线,没有明确的指示牌,没有固定的观演区域,移动中的观众像一群被悄悄召唤的航海者,在不停迁徙的空间里寻找着未知的航线。手机被工作人员收走的那一刻,一种奇妙的转变发生了:你不再是追逐折扣的消费者,不再是刷着社交软件的旁观者,而是一个必须专注于当下、用感官感知一切的“在场的人”。
当我走到二楼俯视中庭时,这一感受变得尤为强烈。演员在一楼的“海岸线”上缓慢行走,而脚下的“海岸线”却随着另一群从观众视角看不见的演职人员的手,在缓缓消失、撤退,一进一退之间,“追随”的执着、“消逝”的怅然、“未抵达”的遗憾,这些抽象的情绪忽然变得可见可触。这种戏剧张力,远比任何宏大的舞台装置都更震撼——因为它没有建造新的空间,而是用艺术的视角,揭露了空间本身隐藏的叙事性。
这让人想起布鲁克《空的空间》“只要一个人走过,这就是戏剧”。但蛇口的空间从来不是“空”的。它是被生活塞得满满的空间——满到你必须用戏剧去重新分配它的能量,才能把它变成“可观看的现场”。所以蛇口的新空间演艺,其实提供了一个对布鲁克的中国式修正:中国不存在空的空间,只有等待被重新激活的空间。
这种激活在《秋日映》中更明显。周末下午南油海鲜市场的半地下建筑空间里,咸腥味、叫卖声、推车轮子摩擦地面的声音构成一条天然声场。蔬菜摊前,一位舞者慢慢拾起面前的番茄,那动作细到像呼吸。“来,帮我选一款健康的沙拉。”旁边买菜的大姐先是愣了一下,随后以自己的经验帮了忙,又继续挑自己的菜。之后两名女舞者叠罗汉在服装摊的镜子前安静地走秀,另一名男舞者推着一推车好奇的小朋友呼啸而过,打酱油群众也只是礼貌地为他们让开了足够安全的通行空间、同时第一时间举起手中的手机。生活与艺术在这里不是碰撞,而是轻轻地互相让出一点位置。这与市面上许多“沉浸式营销型戏剧”形成强烈对比——后者需要人为制造“特意的进入感”,而蛇口的进入感来自场域本身的开放性。

而《我们降落的地方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,蛇口真正的核心,不是场景,而是关系。这部由2025蛇口戏剧节与“海丝新空间”戏剧孵化计划联合孵化的作品,演出场地是“青芒果之家”——1980年代建成的老小区一楼里,一个普通居民的家。房子的主人是发起社区基金会、致力于为这座“他乡兼故乡”申遗的屈红大姐,这里的书桌、书架、阳台与老物件,都沉淀着生活的痕迹。
在这样一个亲切又陌生的空间里,从小在客家花朝戏剧团长大的导演黄冰,用当代剧场视角回溯非遗边缘小语种戏曲从业者的少年梦想。作品以视频影像、身体叙事与纪录剧场结合的方式,呈现了三位平均年龄18岁的少男少女的命运与思考,既有当下的失落,也有对未知的迷茫与期待,而这正是许多地方小剧种与当代观演关系渐行渐远时的共同困境。对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创作者与演员而言,这场演出更像一次观众共同参与的、关于选择与成长的“人生沙盘演练”。
戏剧不是被“带进去”这个空间的,而是在空间的生活与创作者、演员、观众的联结里慢慢长出来的。那是格罗托夫斯基所谓“贫穷的戏剧”所难以涵盖的——不是剥离幻术,而是幻术本来就不存在,真实性反而被放大。

也许是巧合,我看过的本届蛇口戏剧节作品,几乎都是“角色solo+最终汇合”的结构,主题则在“旧日记忆”与“时下生存”之间震荡,演员材料来自自身经验,观众主体性被极度放大。于是我想到:蛇口怕不是正在构建中国自己的“空间戏剧学派”?这既是年轻人和年轻戏剧节的野心,也是实实在在的作为——它不依赖硬件,不依赖预算,只依赖空间与人之间那条被重新点亮的缝隙。

如艺术总监濮存昕所言,每年立冬时姗姗登场的大凉山戏剧节,是国内一年中开幕最晚的戏剧节。大凉山这个成渝等西南都市居民中意的过冬晒太阳胜地,打出了“带着戏剧去旅行”的slogan。大凉山的剧场不是建出来的,而是被大凉山本身构成的。

泸沽湖的湿气、木里香格里拉湖的风、谷克德的山体、冶勒牧羊谷的辽阔,都成为舞台的一部分。那些国外邀请剧目,多被请到被棚子搭起的19号剧场、新村剧场等处,演出时依然可以感到不远处邛海上吹来的和煦微风。而纯朴的当地居民,更是构成这一戏剧节的重要部分。按剧场要求提前15分钟进场,发现好座位上大大小小的外套、书包、甚至零食早早占了座,让人想起大学自习室。
当地观众太过热情,也让习惯了国际化标准运作的演出方必须适当妥协。比如法国痕迹剧团的中国制作人,一遍遍解释“虽然这是小丑剧,但并不适合12岁以下儿童观看。知道您早早占了座,但还是不建议您坐在第一排……”最后也只得提醒因超员而半靠半挂在护栏上的观众请一定注意安全。
作为今年阿维尼翁戏剧节off单元曙光奖最佳表演奖得主,痕迹剧团的这出《美丽床单》,也的确值得。女演员Maly Chhum用白床单这一和人关系最密切的家居用品,一个小时便讲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。至于身体下部掏出的红毛线团,便将月经羞耻和母职惩罚等难以言说的话题一目了然。只消在几个关键点上,一句“帮帮我”、把红线递到观众们手里,就比大多数女权叙事更直抵根部——因为她用的是身体,而不是观点。雅内克说“戏剧不是讲故事,而是在处置身体”,大凉山就是这个命题的绝佳现场。

也许是少数民族地区戏剧节的缘故,来自另一个大国少数民族地区的《阿利夫》,天然吸引众人眼球。舞者在沙地上,用身体写出鞑靼语里那些被政治语言改革消失的字母,继而拼出整首民族史诗。白沙从远方的故乡运来,琴声来自鞑靼斯坦本地传统,一整个失落的语言系统在舞台上被重新触摸。
中国彝族月琴与俄罗斯鞑靼肢体,在和演出同一天举办的川超联赛凉山赛区现场,还来了一次对话合体。那种跨文化的瞬间虽然程序是预先安排,过程却是自然反应生长出来的。福柯称“异托邦”为“现实中存在、却处于制度外部的反射空间”。大凉山正是这样一个地方:国际剧目、民族文化、自然景观、观众的身体,共同形成一个漂浮的共时性。戏剧搭上了文旅的顺风车,却从来不是文旅的附属品,而是文化与自然相互照亮的一种方式。它让我们意识到:中国戏剧的未来,不一定在城市,而可能在更有生命力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,当晚的川超,主队最后时刻被争议逼平,愤怒的主队队员飞踹裁判,似乎也是个隐喻:旺盛的生命力,如何在规则的边界中,达到最大化和合理化的平衡,这是个问题。

不妨再将目光回溯上半年,五一黄金周期间的泉州,全国南戏展演暨海丝泉州戏剧周,则让人看到:传统不是老旧的、需要抢救的东西,而是可以与当代在同一平面上对话的力量。这种对话,既体现在代际传承的鲜活坚守中,也藏在老戏新演的实践里。
府文庙前的广场上,传统与当代的碰撞从未如此自然。木偶戏《驯猴》与AI机器狗跨时空互动,梨园戏“十八步科母”手姿融入街舞,南琶与北琶在《走马》中和谐对弹,古老艺术在跨界中焕发新生。永嘉昆剧《张协状元》、打城戏《火判》等经典剧目登台,前者以朴拙表演再现南戏原生形态,后者用“吐火”特技保留宗教仪式的古朴韵味,让观众触摸到戏曲“何以戏曲”的本质。就连经典剧目《陈三五娘》也推出文旅沉浸式版本,“05后”演员引领观众穿梭古厝亭台,在互动中完成古今对话——不懂戏,平时也不看戏的,也可以沉浸在戏曲带来的美好情绪价值中,这就为明天多一位戏曲观众增加了一份可能。

南戏节发起人、梨园戏代表性传承人曾静萍发起的“年轻演员恢复骨子老戏”计划,更堪称一场“逆潮流”的文化实践。面对南戏“人走艺绝”的困境与青年演员缺乏学习标杆的难题,她与三位青年演员约定用一年时间打磨老戏,最终《白兔记·出猎》《中途遇难》《凤仪亭会》等剧目在展演中惊艳亮相,既保留了干唱、帮腔等古朴程式,又让角色魅力直抵人心。
青年演员主动放弃国家院团的常规排期任务与竞赛评奖诱惑,选择这道“窄门”,让我想起布尔迪厄关于“场域”的论述:“在商业逻辑主导的行业,逆向选择几乎是一种道德实践。”他们的选择仿佛逆着场域的能量流而行,这种“最美逆行”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具价值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,“《陈三五娘》平行时空版”在2023年的蛇口与今年的泉州历经接力孵化后,升级成为《红眠床》,成功跻身2026年香港艺术节的重头戏之列。世界遗产之城的泉州,举办的(非通常由上级有关部门指导的)传统戏曲节庆,其意义正在于此:它让传统摆脱了“遗产”的标签,重新成为可观看、可感受、可触发的当代力量,在代际传承与跨界创新中,完成了对自身的重新定义。
众所周知,香港艺术节是拥有53年历史的东方首个城市艺术节,仅晚于爱丁堡这样的全球艺术节鼻祖。中国戏剧的流动方向,也从“一线下沉”最多是“平层交流”,开始走向“新一线向外扩散”和层级双向流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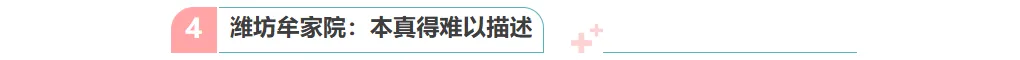
潍坊牟家院乡村戏剧节是我最难描述的一个。不是因为它复杂,而是因为它太简单。简单到格罗托夫斯基所谓“贫穷的戏剧”都显得奢侈,没有剧场、没有节目单、没有观众席,更没有“乡村振兴话术”“文旅包装”“沉浸式”的外壳,只有最本真的生活场景与自发生长的戏剧活力。
这场始于2016年的乡村戏剧节,源于艺术科班出身的返乡青年牟昌非的初心。从小在牟家院村长大的他,经历过进城打拼的疏离与不适,最终因家中梨园的生计难题,萌生了“以戏助农”的想法——既想让城市的话剧与传统的村戏碰撞,吸引年轻人关注家乡,也希望为村庄注入久违的热闹。他摒弃了官方化的“届”,改用章回体的“回”命名,暗合“永远讲不完的乡村故事”之意,一年春秋两季,顺着农时与节气自然举办。

戏剧在这里没有固定边界,全村皆是剧场。抛荒的“城剧场”、废校成了“童剧场”,排水形成高地的“崖剧场”……这些被命名的“问题空间”,既直指乡村空心化、闲置资源浪费等现实议题,也让戏剧重新扎根于土地的肌理。戏剧在这里就像田野里的庄稼一样,自在生长,自然发生:果园是剧场,树枝是舞台的框架,树叶是天然的幕布;打麦场是剧场,麦秸堆是座位,风是背景音乐;废校是剧场,废弃的教室是表演空间,墙角的蛛网是时光的装饰;村民的自家庭院也是剧场,板凳是观众席,院子里的石榴树是最好的布景。
来自各地的剧团与创作者自费驻村,在与村民的朝夕相处中获取灵感,没有预设主题,没有既定剧本,只遵循“自愿、互助、合作”的原则,让作品与乡村真实发生关联。赵川和他的“草台班子”,算是牟家院村的老朋友了。每次都没有预设的主题,没有现成的剧本,甚至没有明确的创作方向。“这帮人又回来了”(村民语)的第一件事,就是住进村里,和村民一起生活:跟着村民下地干活,听他们讲村里的故事,看他们的日常起居,感受乡村的节奏。然后,他们在打谷场做简单的身体训练,村民们好奇地围过来看,有的还会跟着模仿。就在这种自然的互动中,创作的灵感慢慢浮现。

戏剧摄影师李晏至今难忘他们去年五一最终创作的作品:那是一个关于牟昌非父母恋爱的故事。小牟的父亲亲自参演,扮演年轻时候的自己;体验了村民生活的草台班成员主动加入,有的扮演媒人,有的扮演邻居,有的甚至只是在舞台上做着自己的农活,却成为了演出的一部分。没有复杂的剧情,只是还原了父母年轻时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简单场景: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相遇,在田埂上并肩行走,在院子里一起做饭。
但就是这样一部“朴素到极致”的作品,却让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。当小牟的父亲带着乡音努力说着普通话,道出年轻时对妻子的爱慕时;当村民们用最真实的动作,演绎着乡村生活的日常时;当舞台上的场景与村子里的现实重叠时,你会忽然意识到,戏剧的原型一直在这里——戏剧本来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叙述,是对日常的提炼,是对情感的表达。我们在城市的剧场里看多了虚构的剧情、专业的表演,却忘记了戏剧最本真的样子,就是生活本身。

还有一次微型的社会行动艺术:团队打印了30张“高价收购村内老树”的“小广告”,悄悄贴满了全村。“村里的树怎么能随便砍?”“这是谁贴的?”好奇的村民甚至试着拨打广告上的电话。慢慢的,有村民意识到这可能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,和家人讨论起树木对村子的重要性。从困惑到好奇,从讨论到行动,这个过程比作品本身更有价值——它没有强行融入乡村,却通过一次小小的行动,让艺术成为了连接村民的纽带。
牟家院的力量,在于它彻底打破了“艺术下乡”的“献爱心”,不再是“文化援助”的俯视,而是让戏剧在乡村自然生长。这恰恰是中国戏剧最匮乏的品质——不被规训、不被定义,顺着生活的脉络自然生长的发生性。

几千年前,中国的戏剧就起源于乡村的祭祀、庙会、节庆,是生产者自娱自乐、表达情感的方式;只是后来,它被城市带走,被精英化、专业化、商业化,渐渐远离了乡村的土壤。如今牟家院正在把这种本源的力量找回来,证明了不只是农民也爱看戏、也能演戏,而且戏剧在乡村里,能长出最鲜活、最真实、最有力量的样子。